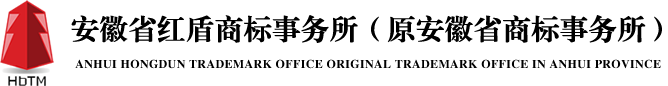深耕数十载破困局:我眼中土特产品牌化的法律逻辑与实践路径
—— 访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与知识产权实务专家、安徽省红盾商标事务所总经理陶爱玲
“土特产的品牌化,从来不是简单的名称注册,而是地域文化基因与法律规范边界的深度融合。” 作为八七届上海轻工包装装潢设计专业科班生,我从毕业分配至外贸单位起,一直深耕品牌规划与知识产权实务已近四十载。这四十年里,我亲手助推过百余款土特产实现品牌跃迁 —— 所谓土特产,是特定地域自然禀赋与人文技艺碰撞的结晶,经百姓代代相传形成 “行政区划名称 + 商品名称” 的约定俗成命名法。但这份 “地域印记” 恰恰成了品牌化的最大阻碍:传统命名与《商标法》的禁令形成天然冲突,如何让土特产既留住 “根”,又踩准法律的 “线”,正是我四十年深耕的核心命题。今天,我想结合实战案例与法律细则,拆解这一破局之道。
命名之初:筑牢合规根基是第一要务
很久以前,我遇见过宣城某县出口换汇的 “XX 芝麻油” 案例:其古法工艺、品质出众,但因名称含县级行政区划,商标注册连续被驳回。后来我才明白,这是多数土特产的共性困境 —— 约定俗成的命名规律,与《商标法》第十条第七款第一项 “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名称不得作为商标注册” 直接冲突。关于可突破注册限制是符合《商标法》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,这一条款其实为这类土特产的品牌化提供了法律出口,也印证了 “使用产生显著性” 的核心逻辑,像当年的 “XX 芝麻油” 若能通过后续运营满足这些条件,并非没有注册可能。
从那时起,我便着力探索合规命名的前置方案和破解路径。经过大量实践验证,三类前置命名方法最为有效。其一,锚定基层地理标识,用乡、镇、村名命名,比如我们曾为巢湖某村策划的 “包家坊豆腐”,既保留地域属性,又符合注册要求;其二,依托自然禀赋取名,浙江 “云雾溪茶”“鹰嘴岩笋干” 等案例证明,山水溪岳的名称自带辨识度,且无商标注册障碍;其三,挖掘文化内涵,安徽休宁 “龙湾御印茶干” ,结合了朱熹题诗与乾隆御赐的本地文化典故,融入了品牌、跻身高端市场。这些方法的核心,都是在 “地域辨识度” 与 “法律合规性” 之间找到平衡点。
破局现存:“图形先行 + 地标收尾” 的双轨策略
但更多时候,我们面对的是已形成固定认知、含县级以上名称的土特产。这时,“硬改名称” 会割裂文化传承与市场认知,“强行注册” 又触碰法律红线。四十年来,我和团队总结出 “图形商标筑基、组合使用培育、地理标志升级” 的三步走路径,这背后正是对《商标法》条款、《商标审查审理指南》要求与核心商标概念的深度活用。
第一步是培育阶段的 “图形破局”,核心是注册集体商标—— 即由团体、协会或其他组织名义注册,供该组织成员在商事活动中使用,以表明使用者在该组织中的成员资格的标志。《商标法》并未禁止纯图形作为集体商标注册,这给了我们突破口。值得注意的是,并非所有土特产都适合同一商标类型:像 “XX 挑花” 这类依赖特定地域技艺传承的手工艺品,“XX 肉夹馍” 这类需统一服务标准的特色餐饮,就格外适合集体商标注册,可通过组织规范成员技艺或服务流程实现品质统一。
就像 “兰州牛肉面” 的拉面人图形、“淮南牛肉汤” 的圆形碗状图形,我们会为地方行业协会设计融合地域符号的纯图形标识 —— 比如为蚌埠市烧饼夹里脊行业协会设计的 “南北分界线” 团形商标,既体现地域性,又具有独特性。图形注册为集体商标后,关键是同步制定《集体商标使用管理规则》,明确产品标准、使用资质与维权机制。我曾主导的董湖粉丝项目中,规则细化到淀粉含量、晾晒时长等 18 项指标,正是这种 “标准先行”,让后续品牌运营有章可循。
第二步是推广阶段的 “组合赋能”,这里会用到未注册商标—— 即未向商标局提出注册申请或申请未获核准的商标,虽不受《商标法》专用权保护,但可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合法使用。我们会指导从业者采用 “纯图形注册商标 + 土特产名称(未注册商标)” 的组合模式规范使用。这里要厘清法律边界:图形是受保护的集体商标,含县级以上名称的土特产名称作为未注册商标辅助使用,既规避了第十条第七款第一项的禁令,又能通过持续宣传积累知名度、培育显著性,为满足《商标审查审理指南》的注册条件铺路。印象最深的是“桐城锌米” 项目,我们第一步征集 “桐城锌米”纯图形与 “桐城锌米” 组合使用,两年间通过线下门店统一标识、线上短视频宣传,相关公众对 “图形 + 名称” 的关联认知度明显提高,完全符合 “相关消费群体中广为知晓” 的要求,这为后续升级奠定了基础。
第三步是升级阶段的 “地标确权”,目标是注册地理标志—— 指标示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,该商品的特定质量、信誉或其他特征,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。这类标志尤其适配 “XX 灵芝”“XX 花猪” 等产品:前者依赖特定地域的土壤、气候形成独特口感,后者与当地养殖环境、传统饲喂方式密切相关,其核心价值与产地强绑定,最适合通过地理标志实现保护。
当组合品牌形成知名度后,具备了《商标法》第十条第七款第二项 “地名具有其他含义或者作为集体商标、证明商标组成部分” 的适用条件,此时申注地理标志成为关键。更重要的是,这一过程中积累的使用证据与知名度,恰好满足《商标审查审理指南》中 “取得显著性”“具有较高知名度” 的要求,与《商标法》第十一条第二款 “缺乏显著特征的标志经使用取得显著特征的可注册” 形成逻辑闭环。去年我们推动的 “XX 市大米” 地理标志注册,正是凭借三年销售数据、媒体报道、消费者调研等证据,证明其已具备显著特征而努力获批中。
行业深耕:法律是工具,共生是核心
在我看来,土特产品牌化从来不是 “钻法律空子”,而是用足《商标法》、《商标审查审理指南》等法律工具与商标概念实现 “地域价值最大化”:集体商标解决 “规范使用” 问题,适配技艺、服务类土特产;地理标志解决 “价值确权” 问题,适配自然禀赋关联度高的产品;而未注册商标的过渡使用,则是连接两者、培育显著性的桥梁。这三者的协同,本质是让 “土特产” 从零散的农户产品,升级为有标准、有品牌、有法律保护的区域公用资产。
四十年来,看着越来越多的土特产通过这套路径走出大山、走向全国,从 “养在深闺人未识” 到 “人人皆知地域牌”,我愈发坚信:破解品牌化困局,既要懂法律与指南的 “硬规矩”、商标概念的 “真内涵”,也要通地域文化的 “软逻辑”,更要守行业共生的 “活原则”。未来,我仍将深耕这片领域,让更多土特产在法律护航下,成长为带动区域经济的 “金名片”。(赵以宝)